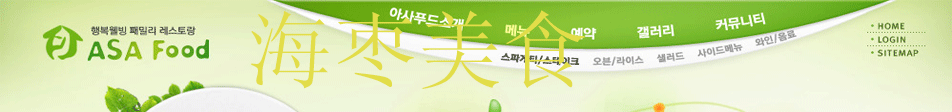时间:2020/11/5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点击:
61
次
在宿舍门口拿本杂志当拍照道具写过很多文字,突然发现自己很少提及自己的插队生涯。是因为写知青岁月的人太多,还是因为曾经的往事是那样的不堪?有时候人会不由自主地在大脑中屏蔽那些太苦太辛酸的往事,但为什么一见到插兄妹,一踏上那片故土,又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有眷恋,终究还是难忘。江西贵溪圳坢林场知青50周年大团聚后,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祭奠我们的林场,祭奠我们曾经的岁月。难忘故土被上山下乡的中学生年我们插队于江西省贵溪县河潭埠圳坢“五七”油茶林场。一大堆前缀主要是地名,之所以叫“五七”,是因为文革前夕的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圳坢“五七”油茶林场在原林业大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专门接收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后来人们把那一系列前缀词去除,简称为“圳坢林场”。可笑的是,当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去林场时,大多不认识“圳坢”这个词,都读了半边音。我们 批下放圳坢林场的上海知青,共64人,大多初中生,年龄都在16、17岁的花样年华,少数高中生才20岁左右,来自于原卢湾区瑞金街道,当时所谓的上海“上只角”地区。说来惭愧,我们这批人都不是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都是因各种原因在里弄待业过一两年的,实在是被当时上门动员的锣鼓声敲得耳朵振聋心发跳,没辙了,才不得不报名上山下乡的。直到今天我们中不少人还留有后遗症,只要一听到锣鼓声响,心就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上海知青在农村的 个家谭汉青就是在锣鼓声的逼迫下,带着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同来圳坢林场插队的。他家兄弟姐妹6人,父亲是工人,每月工资66元,母亲无业。他是老二,上有一个年龄相差10岁的大哥。因为大哥在上海工作,届毕业的他就注定要去郊区或外地农村。紧挨他毕业的是届的弟弟和届的妹妹,这两届毕业分配的方案是“一片红”,就是全部分配去外地农村,而且是到贫穷或边缘的省份——江西、安徽、贵州、云南、吉林、黑龙江。一场文革将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 的经济城市——上海竟然无法安排自己的学子就业、就学。才十六七岁发育未全的中学生全部下放外省农村当农民,这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还没发育好的上海男孩到农村谭家仨兄妹老三届齐全了,却都在家里“吃闲饭”,于是动员的锣鼓队天天挤满了他家所在的小小弄堂。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适龄孩子不去上山下乡的,父母就要停职、办学习班。眼看父亲连区区66元工资也保不住,懂事的谭汉青决定带弟妹走了。大哥舍不得,铺开一张全国地图,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 停在了江西的版图上:“就到江西去吧,离家近些,还可以吃到大米。”一报名,立刻领到了购买脸盆、旅行包和蚊帐的票证。谭氏三兄妹 次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多少有些兴奋。但同时购买三套行装,对父母是不小的负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他们没有向父母要钱,是大哥主动给了些钱。谭汉青去沙发厂购买论斤称的人造革边角料。回到家用纸板打样,擅长手工的他把一块一块碎料仔细地拼接起来,然后裁剪、缝纫、打上铆钉,制成了三个旅行袋、三个马桶包。马桶包是当时正流行的一种背包款式,不少人见了还问:“你这包是从哪儿买的?”。他又淘来木板条,用铁钉敲打,制成了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大的兄弟俩合用,小的给妹妹。妹妹谭雪影同样心灵手巧,没钱置办出行的服装,就用裙子改成衬衫,将短了的裤腿接上一截布料。她还学二哥样,用家里的零碎布料拼成三个枕头套,枕套边还缀上了一道别致的花边。三兄妹的上山下乡,还有为大哥腾出结婚空间的意愿。一家人虽然住在上只角的永嘉路,但家是汽车间,一大一小两间房总共才20平方米,大哥已经有女朋友了,因为无房无法结婚。三兄妹临行前,大哥将自己用3元钱从“淮国旧”(淮海中路国营旧货店)淘来的一台简易照相机,当作珍贵的礼物送给了谭汉青,谭汉青又去淘了一些便宜胶卷。正是因为有了这台照相机和胶卷,后来圳坢林场知青的倩影才留了下来,当时除谭汉青外,64名上海知青中没有一人拥有照相机。谭氏三兄妹同年同月同日离开上海赴江西谭氏三兄妹走后没几个月,大哥就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结婚了。三兄妹都没回来,没钱,也没假。谭汉青刘美芳夫妇重回林场项秉清的下乡更属于无奈,她从小患有哮喘,别人可以持着医生证明在家待业,但她不能,因为她出身不好。其实她的爷爷项松茂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创始人,五洲药厂和固本肥皂厂都是他开设的,年因为支持抗日将士惨遭日本人杀害,今天我们还能在上海历史博物馆看到项松茂的照片和介绍他事迹的专栏。但是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个家族的成员受到太多的冲击,公私合营后项秉清的父亲便被定为“坏分子”。一家人被赶出宽敞的南昌大楼套房,驱逐到长乐路上一个低矮得连家具也搬不进的底楼。文革中她父亲被监督劳动,工资割到了每月26元,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活。一家七口全靠亲友和好心的邻居们接济。连米店、酱油店、水果店的营业员看到她母亲来买东西,也会同情地塞上一大堆东西给她,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小钱。我知道项秉清的名字,是在批斗她父亲的大会上,当时我作为里弄重点动员对象被拉到批斗现场接受“教育”。只见她父亲微胖的身躯,低着头,满脸通红,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他的罪名就是家有两个适龄上山下乡的女儿,结果一个投亲插队到宁波嫁了个地主的儿子,另一个还待在家里,指的就是项秉清。我与项秉清是被同一节车厢拉到江西贵溪,一同分到圳坢林场的,后来同宿舍三年,成了终身的好朋友。项秉清(左1)与她的知青朋友们周晓沪,是我们64人中成分 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年5月上海解放,8月女儿出生,拂晓了,天亮了,父亲给心爱的女儿取名“晓沪”。晓沪是届高中毕业生,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毕业分配时她没有立刻报名下乡,想等一等,看看对独生子女有没有宽松的政策。为了避开上山下乡的风头,父母让她回宁波老家的亲戚家住上一个阶段。年晓沪是在宁波度过的,倒也风平浪静。一年后回到上海,锣鼓声就在家门口敲响了。动员的人对她说:“你父亲已经被打倒,现在是否能得到解放,就看你了!你若赖在上海不走,你父亲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晓沪看到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母亲常常在厨房抹眼泪,感到深深的自责,决定报名下乡去。她的行装是父亲给打理的。父亲是个十分严谨的人,用塑料布把棉被包扎得方方正正,用报纸把木箱里的物件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临行前父亲还给了晓沪一个小闹钟,当时钟和表可是稀罕物啊!是父亲一人到火车站为女儿送行,母亲在家哭得出不了门。火车的汽笛一响,晓沪看到向来刚强的父亲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所以我们这批16、17岁的中学生来圳坢林场,大多都是被逼无奈,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想象中的林场,应该犹如黑龙江大兴安岭,茂密森林,大树参天,但圳坢林场不是,一片红土岗,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低矮的灌木丛,这儿土层很薄,没肥力,也不见机械化操作。油茶一般适宜生长在土层深厚的酸性土,而不适于石块多和土质坚硬的地方。但在人定胜天的时代,什么样违背科学的事人们都敢想敢做啊!之前的林业大队留有一些油桐树的,组建圳坢林场后就拔掉油桐树,栽种油茶苗,口号是“将万亩荒山变成万亩油茶林”,其实圳坢林场根本没有万亩的面积。从上海来的我们根本没见过油茶,也不知道怎么耕种和栽培,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荒山上种植油茶,只知道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当时给我们的指标是每人每天打树洞80个,要60厘米长、宽、高,检验时用60厘米长的竹片两根,组成十字型,放到洞底。我们的工具是最原始的猪八戒用的铁耙。用铁耙在荒山打洞,就像是在铁板上敲钉子,只见火星喷射,石片纷飞,有时一用力连铁耙头也飞了出去。我们个个的手掌磨出了血泡,结起了茧子。树洞打成后便在底层铺些野草,说是腐烂后可充作肥料。然后培土栽苗,树苗栽上后就要浇水,等成活了再松土、施肥。在荒芜的原野上挖油茶洞除了种油茶苗,我们还种两季稻,一季麦,还要种蔬菜瓜果。比起插队在农村的知青,我们除了有食堂不用担心三餐外,劳作上要辛苦得多,一个月只有两天时间休息,还不固定,大多安排在无法干活的雨天。下雨天知青的“时髦”打扮我被分在林场三队,三队离总部一二里路,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境地。这儿不像总部都是新垒屋,我们住在摇摇欲坠的旧屋里。屋前屋后罕见地有几棵泡桐树,泡桐树间还竖着一个标语牌,上面用油漆刷着毛泽东语录“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刚下去时,队里还有一些年下放的上饶老知青,以及从南昌下放的学生和机关干部。圳坢林场成立三个生产队,一队大多是从附近村庄迁来的农民组成的,二队、三队安插知青和下放干部。队长都有贫下中农担当,场领导以南昌下放干部为主。林场总人数不会超过人。我被分配在远离总部的三队。三队知青中数马炳生年龄最小,年下乡时还不到16岁。他特别活泼,那天在三队刘凤根队长举行的欢迎会上,他还高兴地掏出口琴,吹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谁料一天半夜,从小马屋里传出了哭泣声,原来再过几天就是他16岁的生日,睡梦中他想家了。三队的上海知青一合计,决定为马炳生举行一个生日派对(那时还没这个名词,只能叫聚餐)。因为下乡才一个月,每个人的行装中都有父母准备的食品,如酱油肉、香肠、咸肉等,大家各尽所能,小方还取出了当时十分稀罕的梅林罐头厂生产的午餐肉罐头,我们再买了一些蔬菜,就请当地人老陈为大家烹调。年11月23日,马炳生16岁生日的当晚,知青聚餐开始了。我们借来了小木桌,摆在了食堂门口的长廊上,每人带了一个竹凳围坐一起,桌上摆放着十多盘菜,以肉类居多,这在当时当地 属于上乘食品。长廊边的房门一扇扇打开了,人们探头朝我们这边望一望,有到食堂打水的经过我们身边友好地笑一笑。上海知青集聚一起说着家乡话,尝着家乡菜,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油然而生。马炳生的话多了起来,他在异乡的 个生日是上海知青们同他集体过的。三队有不少上饶知青,年龄略比我们大些,他们大多是在年被动员下放的,因为当时的上饶工商业不发达,无法解决城里人的就业,文革前就动员年轻人到周边的垦殖场就业。上饶知青被叫作“老职工”,也许因为对前途的无望,老职工大多早早成了家,有了一两个孩子。经常从他们房里传出夫妻吵架声、哭闹声,贫穷和无望带给成家男女的往往不是甜蜜,而是苦涩,这让刚踏上社会的我们很是心惊。年岁末,为辞旧迎新,也为了欢迎我们,林场大聚餐,食堂准备了丰盛的菜肴。上海知青 次尝到了江西的粉蒸肉, 次喝到了江西的酿米酒,酒醉饭饱中一时也忘了思乡之苦。回到三队驻地我们还在兴奋中,睡下不久忽然被屋前屋后的骚动声惊醒,仔细一听有哭声、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披衣出门,朝着喧嚣声方向奔去,那是上饶知青大佬邹和官茶花的房。进门一看不由得楞住了,大佬邹手足无措地在哭泣,他的妻子官茶花直挺挺地吊在房梁上,脚下是一个踢翻的竹凳。原来夫妻俩因为一些琐事闹别扭,官茶花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赶快用剪刀把绳子剪断,把人放下来。”有人说。“不能剪,要先把人抱下来,再剪绳。”上海知青杨培任说,他知道一旦绳子剪断,突然的压力会使人丧命得更快。官茶花被放在了地上,围绕她的几乎都是我们三队的上海知青,有的大胆地伸手探她的鼻息,有的匆忙地翻着《赤脚医生手册》,那是我们下乡时人手必备的小词典,2.5元一本,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懂急救常识。官茶花的好友、上饶知青小寿赶来了,这位“铁姑娘”胆子 ,俯下身去,对着官茶花做嘴对嘴人工呼吸,不见效果。于是有人赶忙去找场里的章医生。章医生来了,检查一番,宣布死亡。杨培任等人帮着把官茶花抬到了床上。我们几个女知青也就离开了,我抱着官茶花8个月的女儿,襁褓中的女婴还在沉睡中。女知青们都不敢回自己房,一起拥到了我与项秉清的小屋。两张单人床挤着横睡,一张床3人,另一张床4人。官茶花的女儿与我顶着脚睡,她靠墙,我靠床沿,她热乎乎的小脚一动,我的心里就一抽,这个失去母亲的女婴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隔了一天,官茶花的父母从上饶赶来了。林场副主任与三队队长刘凤根张罗着,用杉木为官茶花做了口棺材,并帮着把棺木埋在了三队排屋前的高岗上,没有墓碑。这是我们 次面对死亡,也是我们上海知青到达林场的 堂生死课。也许因为三队远离林场总部,上海知青比较团结,干活也比较卖力。我们白天干活互帮互助,晚上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知青中凡回家探亲的,我们都是集体迎送,挑着扁担走得最欢的是小朱,他的父亲顶着“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帽子,所以他干什么都比别人积极。谁到了上海,就负责为其他知青家送江西老母鸡、花生等,回林场前又去一家家收肥皂、白糖、罐头、衣服等,一带就是十来个旅行袋,我们也因此熟悉了彼此的家人。至今都有那种记忆,每回从上海到达菡潭车站时,头一伸出车窗,见到站台上顾盼张望的同伴的身影,心里就热乎乎的。说起来我们还集体做了一件坏事,我还是领头的。队里有位老职工对我们上海知青总是很看不惯,言行上很是不逊,我们气得闷在了心里,商量着要惩罚他一下,于是决定拿他养的一窝鸡出气。趁回沪探亲我到药房买了一袋老鼠药,回林场后由男知青撒在他的鸡窝周围。第二天一早就听到他夫妇俩的哭嚎:“我的鸡怎么死了哎!”我们几个躲在屋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吱声。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内疚,那窝鸡是当时他家的 财产啊,请原谅当年的我们少不更事吧。藏龙卧虎之地让我们下乡时的名义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到了圳坢林场,贫下中农寥寥无几。回想起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刘队长——刘凤根。刘队长,挺拔的身躯,国字型脸,相貌堂堂,总是赤着脚,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每天一早,他在屋前屋后口哨声一响,我们就跟着他出工了。那时的队长,样样事身先士卒。刘队长干活是一把好手,插秧、犁地、匀河泥、打水沟……都是他手把手教给我们的。不同的是,我们知青都买饭票吃食堂,刘队长回到家还要生火起灶,自己煮饭菜。虽说那时他拿高工分,但也只比我们多了几元钱,又有着四五个孩子,怎么算都属于贫困户,有自留地种的菜,菜票就省下了。但刘队长也真有骨气,看着我们知青从上海带这带那来,他从没开口向我们索要过,也没见哪位知青上他家送过什么。刘队长对知青的管理很军事化,吹哨出工吹哨收工,晚上不时有会议,不是冗长的那种,都是布置工作,总结经验,说完就散会。后来才知道,刘队长当过兵。他一口贵溪话,却听说不是当地人,原籍在江苏宜兴。但刘队长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他的脸上也很少有笑容。因为他的不苟言笑,我们都有些怕他。但印象中刘队长从没骂过任何人,哪怕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的。我是最早离开林场的,没向刘队长告别,但对他莫名地心怀敬意。所以年我出差南方时,特地去了圳坢林场。人们告诉我,刘队长现在县城开了一个小卖部,我就赶去了贵溪县城。见到我,刘队长再也不是往日的严肃,脸上笑容几乎没消失过。他还特地送我去火车站,车子开动前从窗口递上一包食品给我,我推辞着,我都没给他带见面礼啊!刘队长脸一下子沉了:“如果你嫌弃,等我转身后你可以丢掉,但现在一定要拿。”我不得不收下了他的心意。年河潭埠知青下乡30周年大团聚时,刘队长也来上海了,受到大家的欢迎,李桃喜等邀请他到家里作客,我在酒店设宴招待他与另外几位长者。刘队长年兴冲冲来上海参加知青聚会活动年刘队长在女儿(左)的陪伴下来上海参加知青大团聚活动年11月我们部分知青再回圳坢林场,得知刘队长已于当年清明节前因脑梗去世,时年89岁。他的女儿建华拿出了刘队长留下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下了我们64名上海知青的名字,而为首 个是我的名字,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年10月6日部分上海知青团聚照年11月重返圳坢林场在当年的知青宿舍前留影,左4为作者。后来建华请我写家史,给了我一堆资料。我才得知刘队长原来参加过 ,上过抗美援朝 线,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他在部队屡屡立功,年退伍返乡后在宜兴县鲸塘乡政府工作任乡党委委员。年为响应党的号召号召,他退职回乡。不久被抽调参加水电建设任指导员。但在水电站工作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对待。也正在这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村里饿死人了,刘队长的父母也饿死了,为了活命,年刘队长到江西打探,发现江西是产粮省,饿不着。又值上饶林垦处正在招工,于是刘队长回乡后带着一家三口以及亲戚们来到江西。但户口与组织关系被卡在原籍,一家人便成了“黑户”。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黑户”没有了粮油关系生活会遭到很多磨难,而失去了部队的功劳证、复员军人证明、中共党员证明的刘队长,也因此结束了他前半生的所有荣耀,不得不屈尊在圳坢林场谋生。建华说,当年父亲是挑着担子把她带到河潭埠的,才两岁的她坐在扁担的前一个箩筐里,后一个箩筐装着一家三口全部的家当。父亲光着脚板挑着担在前面走着,母亲在后面跟着。路过红薯地,小建华还嚷着要吃红薯。建华不止一次地对我们上海知青说:“我父亲一直
|
------分隔线----------------------------
Copyright (c) @2012 - 2020

提醒您:本站信息仅供参考 不能做为诊断及医疗的依据 本站如有转载或引用文章涉及版权问题 请速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