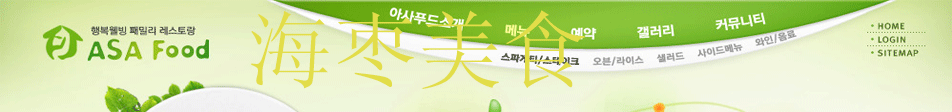|
家乡的腊肉 文 杨光武 天气渐寒,时已入冬。又到铜钹腊肉香飘时。 在我的家乡铜钹山。每到寒冬腊月,那是腊味最好的季节。煮饭时蒸上一碗“腊肉炖蛋”或者来一碗铜钹山笋干丝炒腊肉片,待到摆盘上桌,一家人围坐着吃饭,屋子里弥漫着令人垂涎的腊味鲜香。吃一口饭,咬一口腊肉,享受着那种米饭的香甜合着腊肉的咸香美味,那是山里人最欢乐的时光。 哦,家乡的腊肉 山里人家 旺旺的柴火 熏烤着不肥不瘦的岁月 直到灶台上成串的腊条 溢出乡土的清香 白膘润滑精肉火红 初尝熏味噎人 再尝醇香浓厚 在外的游子 梦里搜索 那熟悉的扑鼻味道 故乡在心里 妈妈在心里 …… 忘不了,小时候我家制作腊肉的情形。那年腊月,杀的年猪是头大黑猪。留够过年要用上的猪肉,剩余的切成一刀一刀的“腊条”肉。我就围着母亲,看她一遍一遍反复清洗干净,沥干、撒盐、搓揉、砌砖样地堆放在一个有盖子的大缸里腌上好多天后,用一根根铁丝穿钩着挂在屋旁的村道边那个竹竿搭建的架子上晒。傍晚,太晚下山后。我和哥哥小心翼翼地将一串串“腊条”肉收挂到厨房烧柴火的灶台上面那个大铁钩上。串串“腊条”肉,一圈一圈叠挂着,远看就像一盏大灯笼。 小孩子就爱好奇心。心里一直想着这些“白里透红”油油的猪肉肉怎么挂在空中,柴火灶只是些烟烟熏熏,又没柴火直接烧烤它,怎么就变成香香的美食腊肉呢?想啊想,就连晚上睡觉还想着。等到妈妈早上起床煮早饭到了厨房后,我就悄悄起床躲在厨房门后看着妈妈生火做饭、加柴。只见灶台烟囱口冒出缕缕烟雾就像天边的云朵朵样绕着、托着、包围着那些腊肉条儿。缠着缠着,不一会儿又丝丝缕缕爬伸进厨房顶的瓦缝隙间不见了。躲在门后久了,两只小脚渐渐有点发酸,弓着背缩颈抬眼的动作弄得全身不舒服。干脆走进厨房里坐在妈妈身边一会儿看妈妈烧火,一会儿又抬头看看那个“腊条灯笼”。妈妈觉得奇怪就问我“你天天睡到热头(太阳)上山晒到屁股的,今天为啥起床这么早,饿了?”我一直摇着头,眼晴却盯着柴火烟熏着的腊肉条。妈妈好像明白什么似的问“想吃腊肉啦?傻孩子!还早呢。”我一听又摇头。妈妈接着问“那你为啥起早啊?”“妈妈!这白白的猪肉没用火烧怎么变成腊肉啊。”“哦,傻孩子!这灶台肚里烧着旺旺的柴火呀,从这烟囱口有热量上去烤着那些猪肉肉呢!还有这柴火烟一天二天、天天熏呀,这猪肉肉就变会颜色,时间久了就成腊肉了,很香好吃又放得久。”我听着却又似懂非懂的,只是听到说好吃,心里就乐了…… 在铜钹山,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腊肉。腊肉都是选用山里农家自养的猪肉,经过盐腌制好,晒或放在通风的地方自然风干后,成串成串挂在自家厨房烧柴火的灶台上面让柴火熏制。平日里想吃就切下一些,洗去柴火灰,用蒸或炒的方法烹调。一碗满是红香的瘦肉里透着油亮玉色的腊肉。下饭时,一口咬下,满嘴流油,香气四溢。 腊肉,在老家请人吃饭时,是可以上桌的菜中一道用以敬客的土特产菜。以前,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妈妈就会拿出一些上好的腊肉,在厨房里忙碌起,清洗、切片、舀匙糯米水酒加几个鸡蛋蒸煮好,待到吃饭时端给客人品尝。 一碗腊肉蒸蛋。透着嫩黄色的蛋黄、玉色的蛋白粘连着那红香的瘦肉带着玉色的肥肉连着皮的腊肉,散发出阵阵烧烤味。特别是远方来的客人吃了过后都说好吃,味香地道。 长大后走出山乡,外出去挣钱,无论路途有多遥远,爸妈都会在远行的背包里放上一包腊肉,并叮嘱,在他乡异地也让身边的朋友尝尝家乡的腊肉…… 一碗腊肉,有着柴火的味道,大山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每每外出,带走的是腊肉,带不走的是爸妈的牵挂。寒冬腊月到,只待游子归! 腊肉,不仅是铜钹山人舌尖上的美味,更是许多在外打拼的铜钹儿女对家乡的记忆,承载着家的味道,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乡愁。 哦,我的家乡腊肉! 杨光武,上饶市广丰区铜钹山人,喜欢看报读书,卖过服装,跑过业务,现在开美发店,是一名发型师,习艺于广州标榜,上海沙宣美发学院。文字,工作之余能静心修身养性!空闲时有文学的日子不会无聊。 欢迎来电咨询 销售 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