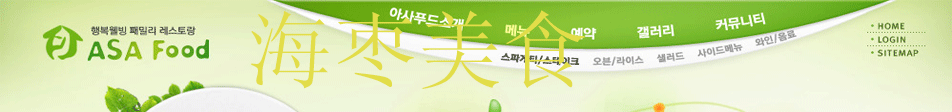时间:2018/5/29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点击:
61
次
原创文学︱NO.15期刘远祥太阳照在丰溪河上(散文)题记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刀耕火种到农耕社会,把土地当作父母,把土地视若生命,默默躬耕,养育了自己,承载了国家。如今土地却让农民得不偿失,纷纷转移外迁,而新一代农民梦却又期待新一轮的土地改革,让改革深耕希望的田野……天空时明时暗,乌云时聚时散,太阳躲进云层里,却不时探出脑袋,把灼热的阳光洒在丰溪河上,洒在我的脸上。空气闷热得让人烦躁,我挑着书箱、被褥,吃力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霹雳一声雷响,狂风卷着乌云滚滚而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上世纪年代,我能有幸地在广丰中学度过6年的校园学习生活。年5月26日,学校停课“闹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到处“硝烟弥漫”,乱作一团,读书的学校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生性胆小怕事,就挑着书箱、被褥回家种田。我家住在丰溪河畔的霞峰人民公社(今霞峰镇)同心大队(今大尖山社区)屏麓村,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整整五年的极度劳累和饥饿锻炼了我,也与乡亲们结下了深情厚谊,更让我了解他们的家史甚于了解自己的家史。从学校回家的当天晚上,年已六旬的三公就来我家屋里坐,他辈份大,全村人都叫他“三公”。三公的身份划为富裕中农,身份虽不响当当,却也是团结的阶级对象,我放心地让他来我家聊天闲侃。三公有两个哥哥,老大村里人叫他大公,已经死了;老二健在,叫他二公。二公身高一米六出头,比三公矮了近二十公分,老实又不会交际人。二公从小身体不好,父母就想让他读书找出路,但他不中用,没读出个名堂。大公身高体壮力气大,三百多斤老秤埔城担挑起就走,百多斤的担子挑个三十里不用歇脚。大公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当过脚夫也当过兵,还在河口码头做过搬运工人,最后又在上饶铁山古道客栈做过大厨,是个十分能干的人。不过这样一个力大心又好的人结局都不大好,因他耆赌如命,输掉了土地、房屋,也输掉了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大板锄头。当他准备将小儿子牛訚卖了筹集赌资再战时,族中长者制止了他。民国三十五年,贫病交加的大公,倒毙在路边的田埂头底,没撑到翻身解放的日子。自然,他的小儿子牛訚在几年后的土改中成了贫雇农。牛訚的身份虽然响当当,但比起自己的哥哥“华訚”(大公长子)还是差了点,因为华訚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老大哥。大公死后,牛訚立即走上了他父亲的老路,成天脚趿破草鞋,腰缠烂汗巾在墟市上赌钱打牌。人们开始议论说牛訚哪天也会同他老子一样倒毙在哪条田埂头底。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得到牛訚的命却比他老子,比屏麓村任何人都好得多呢?民国三十七年(年),牛訚“卖壮丁”当兵以后,刚到战场就被解放军俘虏,由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部队,牛訚学了文化,学了技术,复员后成了县百货公司的经理,一九八六年离休,政府还给了地基拨了款为他做了房子。卖壮丁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穷苦人的无奈之举。但据三公说,卖壮丁也常是一些二流子的勾当。他们收了人家七、八十块大洋后,就替人家去当兵,然后他们从军队中开小差逃出来,有的过后又重新将自己“卖”出去。三公年轻时也当过兵,他在军队没过多久就当了逃兵。三公说他是在一个漆黑夜晚逃出兵营的。在躲过搜捕以后,经长沙、萍乡、贵溪、上饶,一路艰辛,步行八百余里回到霞峰老家。三公的父母也是贫苦的农民。据三公说,他们仨兄弟分家时,每人只分到一亩七分田土。而我回乡时,生产队人均田土是一亩四分。三公最初家境并不好,一亩七分田土的出产,仅能糊一、二个人的口,但要养活老婆孩子显然不行。同时,侍弄这些田土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于是三公一有空闲就去替人当脚夫。沿着九曲十八弯的入闽古道,将茶油、桐油、土纸、烟叶等广丰土产挑到福建埔城、崇安,再挑回食盐等日用杂货,以赚取微薄的脚钱维持家计。从广丰到埔城来回要走好些天。白天,脚夫们挑着百斤重担翻山越岭赶二十几里路,晚上到达投宿的乡间小伙铺。三公说,那些乡间小伙铺不但供应热饭热菜热汤,还有热水给脚夫们烫脚。伙铺的老板对脚夫们十分亲切,老板娘还常与脚夫“打情骂俏”。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过路客商和脚夫们的好感,下次还来住她们的店。果然,那小伙铺还为宿客提供其他隐性服务,例如,只要你肯出钱,伙铺的女佣会为你洗脚,多出点钱的可陪你上床。挣的虽是几个辛苦钱,却仍有脚夫经不起这诱惑,结果是“肩膀上压出糟,抵不上床板摇几摇”。三公那时虽年轻,却不风流。他从不参与伙铺里的牌局。他虽十七岁就结婚娶妻,但起初八、九年里,三妈(即三奶奶,广丰腔称“奶奶”为“妈”。以下相同。)未为他生一男半女。三公既肯干,又节俭,家庭人口又“素净”,这就使他有余钱来贩大米。经几年的积蓄,他终于买来一块虽偏远荒芜,但价钱便宜的茶山。花了一整个冬天的时间,三公将那块茶山垦复了,又听人说在垦复的茶山上种荞麦会有好收成,于是种上荞麦。果然,荞麦收成不错。数年后,油茶树果实累累,茶油产量逐年增加。三公就这样干着。他比大公肯吃苦,又比二公精明,并且后来三妈为他生出了儿子老平以后,从此停止生了,而不像二妈那样接二连三地为二公的家庭添丁加口,直添得家徒四壁,隔夜无米。由于积累快,三公就买来第二块、第三块茶山,仅十年光景,他就拥有了成片的黑油油的油茶林。接着,他又陆续地买些田板,还建了一幢新屋。民国三十七年,他讨了一房小老婆,不过还没等小老婆为他生孩子,天下就换了主。土改时,三公的田土和茶山都分给了别人,小老婆改嫁他乡。牛訚和二公那时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并且工作队的马队长就住在二公家里。“马队长最信任二妈。”屏麓村的乡亲们这样议论。二公是个巴交老实的男人,二妈却是个泼辣强悍的妇人。文革期间,不到六十岁的二妈,一场大病后因治疗不彻底,营养没跟上,身体垮了,从此病歪歪的,但与儿媳吵架时却“中气十足”,嗓门高,口才更不错,也看得出她曾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二妈的心计应当出自她的家族遗传,她兄弟是她娘家的大队支书,其子女一个个的在县城当上了体面的国家干部。二妈的两个儿子虽没能终结农民生活,有幸继承了她的优点,他们都头脑活,善交际,一个做副大队长,一个被经常性地抽调出去修水利搞测量或其他非农差事。三公仍然是个勤劳的农民,不但出工放牛,家里还养猪,生活仍过得比别人的好。年的除夕前两天,他把猪栏里两条肥猪请人宰了放在屏麓村路口卖,准备留一小部分猪肉自家过年。这时,一个叫潘华的女干部带着一帮人来,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义,把三公的两整条猪肉“割”到不知哪儿去了。后来,有人传说猪肉都被潘华这帮人私下分了个干净。一世精明的三公,给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三妈闻讯后,呼天抢地,一边哭,一边骂:“这帮天杀的,一年到头,千桶万桶,千辛万苦,过年自家一块猪肉都吃不上,这是啥世道啊……”这一哭不带紧,却从年尾哭到年头,哭得天昏地暗,听者无不泪垂。从此,三公只为队里放两头耕牛,队里的农事也就完全落到了牛訚和老平这一代人的肩上。牛訚是大公的儿子,他身材高瘦,脚虽有些跛,但干活十分麻利,尤其是插田割稻的一把好手,不过,在人们眼里,牛訚仍是一个“单边手”,因为重大的农活,如犁田、耖田的事他都干不了。牛訚性情温和,实话实说,作为翻身农民,他常说些诸如“如今在生产队出工分到的谷子还不如以前当长工挣到的谷子多”这样的蠢话,但农民们听了却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当时的广播、电影和书藉却不是这样讲的。与牛訚不同的是,三公的儿子老平是个样样农活都拿得起又放得下的“种田手”。另一个“种田手”是金生,队里开教小牛、役使耕牛犁田耖田这样的重活儿,队长只放心他们两个干。冬天进榨油坊打油也只有他们两个能掌油槌包枯饼,其他的只能打杂。而队里阶级成份最高的又恰好是他们俩。老平家是富裕中农,金生本是省立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他的父亲土改时划了地主。搞集体化,尤其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在屏麓生产队出工劳累之磨人,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像。春寒料峭的正月初,为了备耕,农民们当然也包括我这个进过学堂的农民,都要赤脚下到水田里,用手抓猪栏糞、牛栏糞均匀四处撒开,再用脚踏入泥中。刚跳下水田时,至少是我,双脚先是针刺般的疼痛,最后完全麻木。春播时节,凌晨三、四点钟就得下田扯秧,然后插秧,虽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倾盆大雨仍将全身浇得不剩一根干纱。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手脚的皮肤给泡得发白发皱,全身感到象散了架似的。在“三伏”“双抢”的日子里,田里的水给晒得烫脚。而屏麓村的农人们却整天在水田里割稻、脱粒,接着插二季稻秧,既饱受了烈日的灸烤,又饱尝了寄居在稻叶上的虫子的叮咬。什么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无光”?这一辈的屏麓人肯定都有深切体验。在遍地白霜的冬日清晨,大家站立在冰冻的地上打豆子,手脚都冻得龟裂开来……忙完这些,吃过晚饭,即使是在农闲,男人要切猪草,女人得洗刷泡了一天的脏衣服,还有另一大堆全家人的破衣烂裤在等着她去缝补……屏麓这一代农民就是这样劳动着,生活着。他们完全被捆在土地上,“半年辛苦半年闲”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他们尽管从年头累到年尾,可种出的粮食仍不够吃。每当稻谷收割、晒干还未进仓,就被催着交公粮、余粮,剩下来的还不够吃一个季度。我家人口多,六兄妹连同爹娘八口,全年口粮两个月就吃光了。怎么办?我起早摸黑,挥着锄头、铁镐,把所有队上分得的山旯旮自留地统统“田园化”,使旱地变成水田,种上稻谷后,还是不够吃。父亲只好带着我偷偷摸摸地给人家做道士,赚来点钱买高价“私米”吃。那时候,粮食是人们的命根子,稻谷是人们心中的“金瓜子”,只要吃得上饭,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可以干。因此,我跟着牛訚,筑军潭大坝、筑丰溪大堤、造水门大桥、建洋口大桥。这样的拼命去干活儿,居然还挣不到零钱用,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打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出处。这样的苦日子,人怎能出头?后来听说洋口新村有个民发煤矿,于年12月间,我一气之下跑到民发,领导见我有文化又年轻更不怕累,就把我留下了。分田到户的当年,乡亲们种的粮食却是多得吃不完,然而,牛訚、老平、近水、金生这一代人已是强弩之末。近水、金生还没过完两年好日子,都在不满60岁的时候死了,老平命长些,也没活到古稀。而他们的儿子们:剑成、任敏、春来、建平立即就接上了班。大公的孙子剑成、三公的孙子即老平的儿子任敏都是在年代初的两次高考失败后回乡当农民的,几年后成了家,建起了新房子,这可是屏麓村自年以来首次有人住新屋!最初几年,剑成、任敏等这一代屏麓农民过着“半年辛苦半年闲”粮食又吃不完的生活,家里有了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然而,若想在致富路上前进一步却困难重重,直到数年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好田垅长出了高楼大厦,致使屏麓村的人均水田不到五分。于是不少农民开始外出打工,而剑成、任敏、老强(二公的孙子)几个就接手了外出打工的亲友们的田土,他们不再种双季稻,而是种大棚西瓜、蔬菜,外加一季晚稻,这样一年辛苦到头也只能赚点生活费。当然,这一代农民,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村里一些外出副业过得好的,新房、彩电、冰箱、移动电话、小汽车都有,而老强守在田里的三个儿子衰毛、二毛、三毛仨兄弟仍住在土改时分到的旧房子里,都快四十岁了,仍然打着单身。年我退休后,看到屏麓村的剑成、任敏等第三代农民,都年过半百,他们的儿女们也都成年,但都沒接父辈的班,而是一股脑儿涌进城市闯天下去。剑成的大儿子到广东打工的最初两年感觉辛苦,一年春节过后想留在家里跟老爸一起种西瓜种水稻。剑成诙谐地对儿子说:“种田没有油水,不划算。”现在剑成的这个大儿子在珠三角当汽车修理师傅,收入颇高。任敏的大儿子忠伟进城后,先在嘉兴与人合伙开汽车美容店,后来自己开网店做电商,前年在市里一高档小区买了九十多平米的新房子。任敏的二儿子毛毛混得差些,在广东打了几年工后,回到家乡县城里卖起了烧烤。二公的第四代长孙混得最好,大学国防生毕业后在部队当军官。命最差的也是牛訚的孙子,进城后找了份为黑社会看场子的事,却因涉案判了十几年。当前,屏麓村剩下不到百十亩水田,整年不离土的农民只有土仔、土猪俩,好多田地甚至连水田里,长满了杂草杂树而抛荒。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刀耕火种到农耕社会,把土地当作父母,把土地视若生命,默默躬耕,养育了自己,承载了国家。如今土地却让农民得不偿失纷纷转移外迁,而新一代农民梦却又期待新一轮的土地改革,让改革深耕希望的田野。有一天,土仔、土猪听说三都办起了新型的现代农业公司,其模式、效果深受农民兄弟的欢迎,他俩决定拜访参观学习。初春的阳光深情而绵长地洒在丰溪河上,土仔、土猪骑着摩托,沐浴着温暖的太阳,朝着三都农业园飞驰……本期摄影供图︱慧子-END-作者简介刘远祥,上饶市作家协会会员。广丰区霞峰镇人,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耕道教家庭,深受道教文化熏陶。年参加工作,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年退休后,接受中国道教文化再教育。广丰文联guangfengwenlian广丰人的精神高地和文艺态度专注本土文艺,投稿邮箱gfwenlian.白癜风治的好吗白癜风遗传
|
------分隔线----------------------------
Copyright (c) @2012 - 2020

提醒您:本站信息仅供参考 不能做为诊断及医疗的依据 本站如有转载或引用文章涉及版权问题 请速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