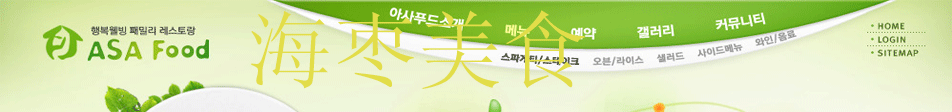|
中科医院专家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附郭城隍庙考——以浙江地区为中心 张传勇 摘要:本文对附郭城隍庙进行实证考察后认为,附郭城隍庙在五代至明初之间曾有少量存在,明中叶开始大规模建立起来。但这两个时期建造的附郭城隍庙,因为所依据的信仰观念不同而有着本质的区别。尤为重要的是,明清时代附郭城隍庙的建造,使得城隍庙建置呈现出“一城数庙”的文化景观。 关键词:附郭;城隍庙;浙江地区 附郭城隍庙是城隍庙建置类型中的一种。所谓附郭或曰倚郭,是指与府州同城而治的县分。附郭之区,其坛庙尤其是城隍庙在设置上与“外属”府县不同,其中有些问题,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小岛毅等已有文章讨论,但到目前为止,空白之处尚多。本文意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对附郭城隍庙的历史作一全面考察,以就正于方家。 一 附郭城隍庙的历史变迁 附郭城隍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受城隍信仰自身发展及外部因素的影响,附郭城隍庙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为从整体上把握附郭城隍庙的历史变迁,并有益于后文的讨论,我们首先对浙江地区的附郭城隍庙作一详细描述。 杭州府钱塘、仁和附郭。两县在宋代已建有城隍庙。《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四《祠祀四》:“钱塘县城隍土地安邑侯庙,在县治东庑;仁和县城隍庙,在县治之东。”入明,两庙皆附府。万历《钱塘县志》“纪制”:城隍庙“附府”。嘉靖《仁和县志》卷七《坛庙》:“本邑与钱塘皆统立于府。” 雍正年以前已附神于府城隍庙。《吴山城隍庙志》:杭州府城隍庙最迟至雍正年间改易为浙江省城隍庙,郡人另祀府城隍于附近普贤庵。乾隆初年,地方士绅呈请易省城隍庙右斋宿厅为府城隍庙,“迎(府城隍)神像而奉之,并迎仁钱二县主之在省主庙者改附于此。” 嘉兴府嘉兴、秀水附郭。嘉兴县庙与府庙同创于后晋。《至元嘉禾志》卷十二《祠庙》:“录事司城隍庙(即明清时代的府庙——引者注)在郡治西一里招提寺西。考证元在州楼上之东偏,晋天福四年立,后移于此地。”“嘉兴县城隍庙在县治内。考证旧在县西二十步,晋天福四年立,后移在县治内之东偏。” 约在明初前后并于府。光绪《嘉兴府志》卷十《坛庙一》引至元志后加按语称“后并于府”。 嘉靖中两县神始附府庙。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十九《祠祀三》:“嘉靖丁未知府赵瀛增葺两廊以居二县城隍之神。” 直至清末未建邑庙。见于光绪《嘉兴府志》卷十《坛庙一》。 湖州府乌程、归安附郭。乌程县庙建于明洪武年。崇祯《乌程县志》卷一《城隍庙》:“庙在县治东数武而近,洪武七年知县孙成建,嘉靖三十三年知县张冕始正庙制。”然成化及弘治《湖州府志》皆无乌程县庙,万历府志亦无“洪武七年知县孙成建”之句。因而,虽然不明“始正庙制”一语之所自出及其确切含义,却足以让人怀疑乌程城隍所居之所,可能建于洪武七年,但至嘉靖三十三年方易为城隍庙。 归安县庙建于明嘉靖年。万历《湖州府志》卷十四《坛庙》:“庙在泰定仓后,嘉靖四十年知县叶恩始正庙制。” 宁波府鄞县附郭。宋元明皆未立庙。《宝庆四明志》卷十二《鄞县志》:“邑附府,故行礼亦附府城隍。”《延祐四明志》卷十五《祠祀考》:“庙以附郭不建。” 清乾隆年立庙。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巳编《古迹》:“清乾隆三十四年始建于今地。” 绍兴府山阴、会稽附郭。宋代已建邑庙。《嘉泰会稽志》卷六《祠庙》:“会稽县城隍庙在县东五步,”“山阴县城隍庙在县东五十步。” 明代新建山阴县庙。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九《祠祀志一》:山阴县城隍庙“旧在县东五步灵承坊,久废。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张明道、知县许东望新建于太清宫侧,与镇东阁对。”会稽县似亦新建。万历《会稽县志》卷十三《祠祀》:“正德十五年知县徐岱修。” 台州府临海县附郭。建于五代以前。《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一《祠庙门》:“城隍庙在县东一百步,吴越时封兴国侯;端拱元年令王子舆重建。” 至明未废。康熙《临海县志》卷二《建置》:“明洪武二年改封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三年改称临海城隍之神。” 金华府金华县附郭。明弘治间建庙。万历《金华府志》卷二十三《祀典》:“在通远门内县南三百步,弘治间建,嘉靖二十三年毁于火,次年知县李庶重建。” 衢州府西安县附郭。始建不详,宋绍兴年间废,明隆庆年重建。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四《祠祀八》引《西安县志》:“在县南五十步醋坊巷。县旧有城隍庙,及建府,即就旧庙立祀。明隆庆五年邑令梁问孟以县不立庙终属缺典,捐俸修造。”又嘉庆《西安县志》卷四十三《祠祀》:“旧志,在县治南醋坊巷。宋绍兴间移建州城隍庙于龟峰,县庙遂废。明隆庆五年知县梁问孟以县不立庙终属缺典,乃倡建于醋坊巷旧基。”即在邑庙之外另建州庙,与《浙江通志》所言易县庙为州庙有异,未知孰是。 严州府建德县附郭。邑神先附府庙,崇祯中建庙。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四《祠祀八》:“在县治东,向附祀于府城隍庙,崇祯丙子知县吴洪昌建梯云楼三层,癸未年知县杨宗简改为县城隍庙。” 温州府永嘉县附郭。邑庙创始无考,弘治《温州府志》无永嘉县庙,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祠祀志》称“在开元寺东,旧在城南厢,久圮,附祀于府。万历甲戌邑令刘三宅改县东仓故址为庙。” 处州府丽水县附郭。邑庙建于乾隆年,前此附神于郡庙。同治《丽水县志》卷五《祠祀》:“在圭山南麓,向无祠宇,附神位于郡庙。国朝乾隆二十一年知县陈创建。” 上述浙江十一府附郭城隍庙的历史,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杭州、嘉兴、绍兴及台州的附郭县在宋代已单独建有城隍庙;第二,明代以前即拥有城隍庙的附郭县,除台州府临海县外,在入明前后都已废弃;第三,除去湖州府乌程县在洪武七年立庙一说尚存有疑问外,所有的附郭县在明代中期以后相继创建或再建城隍庙。大体而言,附郭城隍庙基本上经历了创建——废弃——再建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所要解答的问题是,绝大多数附郭县在宋代都没有单独立庙的情况下,杭州等四府(州)首邑为何拥有城隍庙?这些庙宇后来为何废弃?明代中期以后附郭县大都建起城隍庙的原因是什么? 二 宋元时代的附郭城隍庙 附郭城隍庙问题是与一城之内建有一座以上城隍庙的问题一道提出的。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卷八中提到,“负城之邑,亦有与郡两立者,独彭州既有城隍庙,又有罗城庙;袁州分宜县既有城隍庙,又有县隍庙,尤为创见。”所谓“负城之邑”即指附郭县,其中列举的情况,正如小岛毅所说,已经说不清了。 美国学者戴维·约翰逊利用元代以前的史料,列举了唐宋时代的一百五十多座城隍庙,其中有九个城市建有两座以上。当然,包括了附郭的情况。但约翰逊并没有说明,为何在附郭的城市中存在两座以上的城隍庙。日本学者小岛毅虽然指出了约翰逊的不足,却没有着意填补。在《城隍庙制度的确立》一文中,附郭县单独立庙同县城以外的城市如镇等也有过城隍庙的事实一起,被用来说明“城隍神不是城市自己的神,而是被认为适应包括了乡村的行政地区的神”。 约翰逊列举的九座城市,经小岛毅清理,其中的四座得到确认: 其中两个城市(剑浦县、黎阳县)可能是由于他(指约翰逊——引者注)看错史料,把一个庙重复地数了两次。关于饶州,只看他列举的《夷坚志》中的记载,不能完全证明单独存在别的庙。关于彭州,作为另外一个附郭的庙,《宾退录》中有记载,可还说不清楚,因为没办法靠别的史料做旁证。关于开封府,是在大内(皇城)中有第二个庙,好像是因为首都的特殊情况。笔者能完全确定的只有根据宋元地方志的四个城市,即临安府、嘉兴府、绍兴府、台州。 这四座城市都在浙江,并且都是因为附郭县单独立庙而拥有两座以上的城隍庙。这也是我们以浙江为例探讨附郭城隍庙的原因之一。在约翰逊列举的一百五十余座城隍庙中,差不多有一半建于府(州、军)治,但其附郭多不立庙,上述四个府(州)的附郭县为什么偏偏建有城隍庙呢? 这是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因为当时虽有人提到过这一现象,却很少从正面讨论。相反,有一些言论表明,附郭之区是无需设立坛庙的。宋代湖州附郭归安县无厉坛,《嘉泰吴兴志》注云,“倚郭县不设,附郡厉坛同祭。”宋代浙江各府首邑多建社坛,宁波附郭鄞县亦然,见于《宝庆四明志》,但到了元代,却被认为“社坛、风雨雷师坛以附郭未建”。这表明,社坛、厉坛等坛庙被认为是各府县应建的坛庙,但附郭是例外的。城隍庙亦是如此。鄞县在宋元时代不建城隍庙,被解释为“邑附府,故行礼亦附于府城隍”,“庙以附郭不建。”西安县城隍庙在西安升为州治后改易为州庙(或因新建州城隍庙而废堕),是又一明证。建有城隍庙的临海县,在宋端拱元年重建前亦曾遭到质疑,邑令王子舆下车伊始,祭斯庙,因问有司曰:“邑居郡城,庙从何得?”甚而怀疑“庙非庙”。而与单独立庙的首邑相比,绝大多数附郭县未建庙的事实更可证明,在宋元时代,附郭县不应建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由此看来,四座单独立庙的首邑所以会立庙,想来应与它邑有不同之处或曰它邑所不及者。 城隍神作为“城”与“隍”的化身,有保城护民的职能。所以,建城必有神为之主,有神必有祠庙以居之。在每一座带墙城市中,都应建造城隍庙,这成为建造城隍庙的基本依据。就宋元时代地方志所见,很少有例外。仅就唐宋时代的府州城而言,往往在城中复建城池曰子城,作为府州治所,浙江十一府州莫不如此。但是在绍兴、台州、嘉兴这三个建有邑庙的城市中,我们看到在子城之外,各首邑治所亦建有城墙: 绍兴府,《嘉泰会稽志》卷一,“罗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隋开皇中杨素所筑,“子城周十里,”宋嘉祐中刁约奏修。附郭县山阴与会稽皆有县墙。《嘉泰会稽志》卷十二《八县县境》:会稽“县墙周二里二十步”;“山阴县墙周一里八十步,高一丈二尺六寸,”注云:“见旧经,今不存。” 台州,城内另有子城,州署居焉。《嘉定赤城志》卷二《地理门》说县治原亦单独建在一内城中:“按县须知,周回二百九十五步。按县治附州城,他无郛郭,或云今左右缭墙沿城隍庙至天台馆达上古巷,其步数实合,意旧有城而后易为墙也。” 嘉兴府城,《至元嘉禾志》卷二《城社》:“按旧经云罗城周回一十二里,高一丈二尺,厚一丈五尺。子城周回二里十步,??圣朝至元十三年罗城平,子城见存。”附郭嘉兴县,“县城,按旧经云周回二百二十五步,宋淳熙间仅余一百步,今皆无之矣。” 另外,小岛毅未予确认的开封城,也有三套城墙,罗城套里城,里城套宫城(大内)。因此,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府(州)、县城隍庙与各城墙之间是何种对应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府(州)城内不止一座内城的存在,导致了不止一座城隍庙的建造。我们还不能说明杭州城拥有三座城隍庙的原因,因为现有文献并不能提供钱塘、仁和两县曾单独立城的确切证据。不过,信仰是复杂的问题,有异例是正常的,假使杭州地方在未建有县城墙的情况下设立邑庙,另有其因,大约也不会动摇上述推论。 杭州、嘉兴、绍兴各首邑城隍庙废弃于何时,并没有明确记载,依据方志资料,大致可作如下推论:杭州府最迟至明初前后,嘉兴府在元末明初,绍兴府至迟到明初,大体都在元代后期至明初之间。在这一时期,出于什么原因,这些附郭庙遭到废弃? 虽然城隍庙与社稷坛等都被认为附郭者不必建,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附郭社稷坛之不建,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可能是它们在明初被明令罢建时所说的“烦渎”。首邑城隍庙之不建有同样的问题,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由于笔者对宋元时代的资料掌握不够全面,有些问题,比如除了上述几城外还有无其它建有城墙并拥有城隍庙的附郭县等,尚不得而知,只能就既知的上述几座城市的情况,对附郭城隍庙的废堕原因作些猜度。 就绝大多数附郭庙与县墙有关,以及城隍庙与城池的固有关系而言,似乎可以断定,这种附郭庙应是城隍神原始品格的极端表现形式。由此可以想到,附郭城隍庙因县墙而建,当经过战争或其它原因的毁坏,唐宋时代修建的附郭县墙,如前文所见,至元明之际已多不存。而人们的观念当中,仍然坚持一城之城隍神不应有二。这种观念可以明代中后期附郭城隍庙大量兴建之际的一个事例为证,山阴与会稽为绍兴府附郭,两县在明代中期重新建起城隍庙,万历《绍兴府志》的作者颇为不解,“按城隍神者以城及隍而立,今两京有都城隍庙,其府若县不闻别有祀也。山会两县既系附郭,则与府同一城隍,乃复有此二庙,殆不可晓。”正说明与府“同一城隍”即同城而治的附郭县不应自有城隍神,也不应另建城隍庙。这样,当旧有的县墙成为历史陈迹,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因县墙而建的附郭城隍庙有的可能就会因此而废堕。 在城隍信仰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哪一个朝代明令附郭县修建或不建城隍庙,即使是在城隍神制度化的明代。但是,明清时代的方志大都要提到附郭不立城隍庙,较早者如嘉靖十七年殷士儋《重修济南府城隍庙记》:“州县各有专祀,惟附郭不更设。”嘉靖《浙江通志》卷十九《祠祀志》亦云,城隍庙“各府州县俱设,??其县附府者不另立庙”。那么,这里所说的附郭不立城隍庙所依据的是什么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四的记载很引人注意,洪武十八年秋七月,“己卯,礼部议天下府州县先师孔子及社稷山川等祀,如县之附府者,府既祭,县亦以是日祭,诚为烦渎,自今县之附府者,府祭,县罢之。诏从其议。”正是这一诏令,使得附郭县从前的社坛等坛庙遭到了废弃,如会稽县社稷坛,旧在县南礼禋坊,“明制,凡县附于府者俱陪祀于府坛,县坛遂废。” 作为天下通祀诸神之一,城隍神也应在罢祭之列。但在明清时代,城隍无专祭,惟春秋附祀于山川坛。因而罢祭者当为坛祭之城隍神,至于城隍庙,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存与废都是两可的,因此可以说,如果有存留至此时的附郭城隍庙,或者会因此而废弃,或者像台州临海县城隍庙,入明后一直保留下来。 三 明清时代的附郭城隍庙 明代中叶以前,除了极个别的附郭县拥有城隍庙外,绝大多数附郭县没有自己的城隍庙,方志中常用的说法是“附郭不别为庙”。当然也没有自己的城隍神。在这种情况下,附郭县官员随府官拜谒府城隍庙,如惠州府首邑归善县“官从祭,不立庙”。 但是,从明代中叶起,人们开始强调城隍神与地方官的对应关系,附郭县开始拥有自己的城隍神及其庙宇——城隍庙。如西安县于隆庆五年重建城隍庙,郑大经作记云,“有郡则有守,有邑则有宰,固未尝以郡守而兼摄乎邑令之政,则城隍之神亦当尊卑相承以钦若乎帝天之命,不宜独以郡而摄乎邑也,且如外邑惟龙、江、常、开,其冥司亦未必统于府城隍矣,乃皆各自立庙,西安为五邑之首,顾不得专立一庙以祀城隍,而使昔日受封之神久抑于冥冥,岂非阙典乎?”苏州府首邑吴县于万历二十三年创建城隍庙,崇祯十三年知县牛若麟作记,以为“郡有神则县亦有神矣”,故吴县立庙“于义诚协”。明崇祯十年广东韶州府首邑曲江县创建城隍庙,潘复敏记云:“今宇内郡邑各建庙而虔奉”城隍神,“独曲江以附郭不设。嗟乎!使有郡庙而邑庙可废也?则凡有守之地,朱辎缯盖青绶银章足以控辖一方矣。何以二千石临于上而必藉百里之郎官以佐焉。且如姑苏、如檇李、如吾之於越,特置二令,俾共承其流,合宣其化,即庙亦有二,何独于曲江而缺焉,不讲其义何居!”山东莱州府首邑掖县城隍庙约建于嘉靖年间,不久即废弃。知县杨祖宪以“郡与县不相兼,幽之有神犹明之有官也,有郡守而无县令可乎?”乃于道光十九年选址另建。所有这些言论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城隍神与地方官的对应关系,并以之作为建庙的依据。 这种强调附郭县应有其神的观念,实源于明初的城隍制度。明初洪武二年大封天下城隍,使城隍神实现全面的等级化。次年六月的撤塑像、立木主、庙宇陈设比照当地衙署,进一步增强了城隍神作为“冥界地方官”的职能。作为这一制度的合理延伸,各级官僚机构都应有与之对应的城隍神、庙,这实为附郭县建庙观念的实质。 有一地之官,即有一地之神,所以附郭县逐渐拥有了城隍神,并建立了城隍庙。总体而言,在拥有城隍神后,出现如下几种情形: 同时建起庙宇;附神于府庙;先附于府庙,而后单独立庙。 附郭县在建庙前,城隍神往往附于府庙,从理论上讲,应该有另外的情形,即附郭县在拥有城隍神的同时即建起城隍庙。但是由于方志记载的不明确,欲确认某一附郭县在建庙前不曾存在城隍神并附之于府庙,是极为困难的,因而不能举例证之。 杭州府与嘉兴府是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分别代表了附郭县城隍神附于府庙的两种形式。前者是首邑城隍神与府神同列大殿,而后者首邑城隍神居于府庙侧庑,因独居一室,此庑亦有被视为邑庙者,即如嘉兴府城隍庙于嘉靖中修葺两廊,“以居嘉秀二县城隍之神。”陆杰作记以为:“太守朔望率其属谒庙,已,县令复率其属各谒于所主之庙,制合于宜。”又如福州府,乾隆府志说,首邑侯官县“城隍庙在府城隍庙东庑”,闽县“城隍庙在府城隍庙东庑”。 但有一些附郭县并不满足附神于府庙的状况,或者并不认为邑神所居侧庑可称为邑庙,因此选址另建城隍庙,这就是第三种类型了。如处州府丽水县在乾隆年创建城隍庙前,附神于郡庙。华亭县为松江府附郭,“县以附郭不设庙祀,向于郡城隍庙东西两庑列三县城隍神司。”但到崇祯二年选址另建邑庙。湖北德安府首邑安陆县城隍庙旧在府城隍庙大门内,乾隆三十六年知县高质义谒庙,以为“乌有县而不专作城隍庙者”,遂捐俸创建。在这里已不单单强调“郡有神则县亦有神矣”,而是进一步强调附郭城隍神应自为祠庙。九江府首邑德化县于嘉庆年建城隍庙,此前“县城隍乃仅附于府庙之殿侧”,邹文炳《德化县城隍碑记》云,“县之有城隍,犹之有县官也。县官理其明,城隍理其幽,县官分立曹署,不能寄治于府;县城隍崇饰庙寝,不能寄治于府城隍,幽明之道,本无二致,此理之因乎时起乎义者也。”正是这一观念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证明附郭城隍庙之当建,邹文炳引洪武敕令说:“明洪武三年敕封府县城隍为侯伯,于是各府县分立庙以祀城隍,虽附郭之县亦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就浙江而言,在清代中期以前,各府首邑都已拥有城隍庙或附于府庙的邑神。由于城隍信仰在浙江一带出现较早发展充分,故而该地附郭县立庙的进程并不能代表各地的一般情形。其它地区,附郭县立庙的进程要迟缓得多。如山东地区(见附文),至清末时,所属十府之附郭县,有两县从文献资料中未见拥有城隍神,另外尚有四处未单独立庙,并且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清代中期以后,虽然其中有三处是清雍正年升府的,但设府较早的七府中,也只有兖州府滋阳县建起城隍庙,与浙江相比,显示了地域差异。 由上文可见,宋元时代的附郭城隍庙与明清时代的相比,在数量上存在差别,且所依据的信仰观念不同,前者依据的是城隍神的原始品格,即一城必有一神主之的自然神属性,位于府城内的首邑治所另立城墙时,就有可能建立一座与这一所谓邑城相联系的邑庙;而后者所依据的则是城隍神的社会神属性,即有一地之官必有一地之神,必有首邑城隍与首邑官员对应。所以,附郭城隍庙由宋元时代的少量存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废堕,至明清时代的普遍建立,看似同一历史事物的重复或发展,其实二者有本质的不同。不仅如此,由这两种观念的反差及其实践,可以识见明代中期以降附郭城隍庙之建在城隍信仰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原先一城应由一位城隍神主之因而只能建造一座城隍庙的做法,至此首先在附郭之区打破。从此以后,中国城隍信仰发展史上开始呈现出“一城数庙”的文化景观:附郭之区,一城之内有府城隍庙有县城隍庙甚至省城隍庙;不同县治同城或军事、行政机构同城而治而建有数座城隍庙等。这就使得原先较为简单的城隍庙建置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是明清时代城隍信仰的又一比较大的历史变动。 附:山东各府附郭城隍庙的建造历程 济南府历城县附郭。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四《建置考二·坛庙》:历城县城隍庙,“嘉庆十五年创建于南关东舍坊玉皇宫内东偏,道光七年移建于城内广丰仓之西。” 泰安府清雍正十三年升府,泰安县附郭,未建邑庙。据后世文史资料载,最晚至清末,以县神附府庙(柳方梧《泰安城隍庙略考》)。 武定府清雍正十二年升府,惠民县附郭,未建邑庙(光绪《惠民县志》卷十《坛庙》)。 兖州府滋阳县附郭。邑庙创始无考,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祠祀志》:旧在东关龙王庙左,万历戊午滋阳县知县改建于城西南隅。 沂州府清雍正十二年升府,兰山县附郭,未建邑庙(民国《临沂县志》卷四《秩祀》)。 曹州府清雍正十三年升府,菏泽县附郭,乾隆二十年建邑庙(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二《建置》)。 东昌府聊城县附郭,未建邑庙,弘治间重修府庙,“肖州县城隍以示统属”(嘉庆《东昌府志》卷十一《建置》)。意其中有聊城县神。 青州府益都县附郭,未建邑庙,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三《营建志上》:嘉靖十五年,与外属州县城隍神配享府庙。 登州府蓬莱县附郭,未建邑庙(光绪《蓬莱县续志》卷三《文治志》)。 莱州府掖县附郭,邑庙初创无考,嘉庆《续掖县志》卷一《坛庙》“废祠”条下有“县城隍庙”。道光《再续掖县志》卷上《坛庙》:道光十九年知县杨祖宪倡捐新建。 文献来源:《世界宗教研究》年第1期,第63-71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张传勇,年10月生,山东邹平人,年聊城大学本科毕业,年至年,在南开大学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史。 编辑:王洋洋 审校:张书铭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