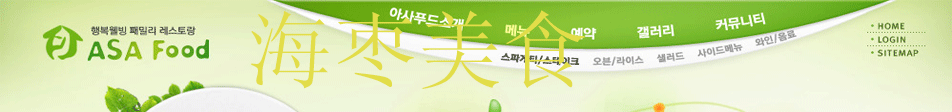|
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第期 钻石之恋刘诗良 静海流深。年,是母亲鲐背之年,亦是父母亲成婚70周年。七十年钻石婚,个日子,小时,22亿秒,一句情比金坚、白首偕老不足以形容与概括他们跋涉的万水千山。从青丝红颜到苍苍白发、沧桑容颜,父母亲相厮相守的70年,打磨了一颗时光之钻、爱情之钻。 大红花轿 年的一个黄昏,西边晚霞正艳,夕阳正红。火红的绸条在晚风中飘拂,一顶两人抬的大红花轿,晃悠在广丰少阳石亭往大石十字垄的乡野小道上,过坎涉水,攀山越岭,迤逦而行。 此刻,蒙着红盖头、感受一路颠簸坐在小花轿里的,就是我20岁的对新生活一无所知而又满怀憧憬的母亲。 这一路,弯曲,陡峭,有时甚至足临悬崖或深渊,就像母亲日后的人生旅程。 外公认准的亲家是他的亲姐夫,相中的女婿即我父亲,是爷爷亡妻留下的血脉,外公的亲妹妹就是父亲的后妈。 “汗金老实,内向,是刘家唯一男丁,放心,起码不会被抓壮丁了,不会妻离子散了。他父亲刘学国勤勉有加,田地富足,难得的好人家,不会愁吃愁穿的。”外公叭嗒一口旱烟,盯着外婆清瘦而白皙的脸,朝天空呼出一个圆圆的烟圈,像卸下了一桩沉重的心事。 酒散客退,身佩红绸、一身喜气而沉默寡言的父亲步入洞房,轻轻掀开红盖头,母亲举首,俏丽的脸庞隐露威严。 首次相见,就是洞房花烛夜,四目相对,是欢喜?是羞涩?是慌乱?两人的心,此刻就如桌上跃动的烛火。 母亲不孕 一对新人不可能预料,大红喜字背后,苦和难两个魔也从此缠上了他们,考验着他们脆弱不堪甚至不值一提或者说根本就是虚无的爱情。而他俩从此便把自己与对方绑在了一起,再没考虑过要分开。 婆婆就是姑姑,亲上加亲,母亲并没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我的后奶奶精瘦,精明,我小时见过她,眼似苍鹰,面如冷月,声音尖厉,长相尖刻,对母亲并不例外。 桃谢荷开,秋尽冬来。土地改革,爷爷田地被分,幸好没有雇佣人力,没被打成地主,而划入了中农。日子看似如外公所料,微波小澜,未撼筋骨。 老屋一角的苦楝树,花谢果已黄,叶盛花又开。年复一年,母亲的肚皮平坦如镜,迟迟不鼓。后奶奶的目光一日比一日锋利。 母亲不敢声张,婆婆和村人的目光像一把把尖利锋快的刀,插向这个远离父母、不谙世情、娇弱而硬气的女子,她偷偷四处寻医求药,一包包、一捆捆的中药不敢往村庄搬,不敢往婆家搬,就往她嫁在附近汤家的大姐家搬,不停地熬啊,不停地喝啊。 四五年后,老天也看不过她喝下的那么多苦水了,开了眼,不知是喝下了第几麻袋的中药熬出的苦涩的药,母亲的肚子终是起了反应。每隔三两年,就下个崽来,一下就是八个。 父亲瘸脚 没崽时是思崽的苦,崽多时是养崽的苦。母亲一下了大红花轿,苦字就粘着她不走了,难字也跟着来。 生儿育女的喜还没延续两年,父亲出事了。27岁时左脚踝因被田地里的毒气侵入,烂开一个小洞,医生看了,土方偏方也用了,溃烂没痊愈,脚筋烂断了。父亲打那后左脚只能以脚尖点地,瘸了,挑不了重担子。碾米、挑谷等乡村重活就落在母亲肩上。原本双人抬的艰难的生活,压在母亲一头尤显沉重,这慢慢撞击出了她脾气里的火暴与泼辣。 一次挑谷碾米,越一竹篱笆时,前箩筐搁在篱笆上,瘦弱的母亲左脚跨过篱笆,踮起脚尖一边扛下前箩筐,一边使劲提上后箩筐,不料用力过猛,一个趔趄,右脚踩上篱笆又急速滑下,一根尖利的竹片直插小腿肚,顿时血流如注。母亲返家草草处理,后来外伤愈合,一截竹片却残留在了腿肚里。几年前,她还撩开裤脚,摸摸,说,硬硬的,还在哩。 刘家祖屋位于村庄中心,前后两幢,木板房,黛黑瓦,煞是气派。刘氏家族多少年开枝散叶,两幢老屋已挤满大大小小10多个家庭、近百口人。 户多房少,口多粮少。村庄四周的山光秃秃的,柴火被砍光了。挑煤是父母兄长们最刻骨铭心的梦魇。一早三四点钟,母亲黑灯瞎火热点饭食,父亲、兄长匆匆扒两口,肩压扁担摇晃着箩筐、畚箕,披着夜色、星光上路,深一脚浅一脚去十几、数十里地外的廿三都上孚煤矿或枧底东井煤矿,拣煤,挑煤,步行一趟,就是一个多时辰,又得挑着重担往回返。一次,13岁的大哥和伙伴回时已是天黑,母亲和村人一块去路上探望,同伴们看到救兵都笑了,被重担磨破肩皮的大哥一见了母亲,艰辛、委屈的泪水随着一大声“哇”,肆意流淌了下来,哭成个泪人。 大姐悬梁 我上小学时,我们这个小家已10多口人,挤在老屋的三个小房间里:中间一间北边放了两口装粮的大瓮,就只安得下一张床,一到晚上,母亲、三姐、妹妹和我就挤在这一张床上;前面一间是大哥和二哥的新房,中间只拉着一道布帘隔开,空的一点空间,还被一个竖打的地窖占去一块地盘;后边是矮矮的、窄窄的、长长逼仄的一条,原是羊圈,大人得低头进,小孩手一伸就可摸到房顶的石棉瓦,父亲和三哥他们就缩住在那里;大姐出嫁了。 大姐为人大方,性格开朗,是我们八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开心果,常常笑嘻嘻的,人又俊俏,嫁给离家三里地的一个篾匠,小日子滋滋润润的。她去了街上,回娘家来,就坐厅堂里,嘻嘻嘻地讲她在街里的见闻,身边围满了人,这时,父母亲也爱站在一边,看眉飞色舞的大姐讲古似的表演着,常常也跟着笑出声来。那是父母清苦日常的一种调节和润滑。 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我在大队部门前空地上,和一群小伙伴嬉闹追逐,笑声在整个村庄回荡。猛然回头,惊见母亲长发飞扬,疯了似的弓腰箭一般地朝村东飞射而去。暮霭沉沉,夜色急降。那个总洒落银铃般笑声、这时却饱受产后抑郁的大姐,抛下她月子里的孤儿,悬梁自尽。正值壮年的父亲、母亲,终日郁郁失声,悲哀落泪。 建造新屋 父母亲在与生活的对抗中越来越坚韧,他们就像硬度极高的钻石,深入生活的矿脉中勘探幸福。年一个清晨,天灰蒙蒙的,细雨纷飞,母亲、父亲领着在家的三姐和我,扛锄,挑畚箕,拿铁镐,上了村西边的晒谷场。那是一块满是麻铺石的高地,母亲说要把它削下一人多高去,做我们的新屋基。 人力挖不动的,只能求助炸药。请的是邻村南山坳经验丰富的老炮工“夹目瞅”。“夹目瞅”那时约五十开外,有点耳背。一次放炮时,他点燃引线跑慢了一步,被炸开飞溅的石块压住了腿,一脚趾被截断,腰也闪了。屋未奠基,人先受了重伤。医院住院,并留下照顾,炮工说:“你家建房是大事,一个大劳力搁这花不来,叫个小孩来就好了。”他老婆专程到我家找母亲,叫我家建房的事别因此停下,人力不够时,让母亲叫三哥和我两个小医院病房换下父亲,照看她丈夫。 大哥去宜春做石匠了,二哥去浦城做篾匠了,父亲中了田地里的毒气一只脚跛了。但这并没阻挡住母亲的好强与坚忍,每天上学前、放学后,母亲领着我们在家的孩子,一人一担畚箕,一个跟着一个,去两三里外的山上挑用炸药轰炸下来的垒墙用的石块,常常是母亲领头,后边跟着11岁的三姐,再后边是9岁的我,天天和着鸡鸣起床,踏着晨露上山,踩着月色回院,我已记不得那时4岁的小妹每天一个人都上哪玩去了。 新房刚搭好框架,地上还一派零乱,那是村里的第一栋红砖瓦房。父亲支了一个棚,月夜下在新屋门前地隙手植下一株半人高的柚子树苗,在屋侧空地移种了三两株翠竹,晚上一个人驻守工地。 偶尔夜深人静,和母亲同住老屋的我,会被一阵拨弄门栓的声音吵醒。“叩、叩、叩……”我知道又是父亲,我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他总是偶尔会这样来吵我们一下,我以为他和母亲是不是白天没吵够,晚上也要来整一整母亲。每次我和三姐都在惊骇中蹑手蹑脚地下床,找来扁担、锄头什么的,把门顶得更紧闭、更牢实。我不知母亲醒了没有,她不说话。但这些只是徒劳,在我朦朦胧胧的睡意中,门总会在父亲锲而不舍的拨弄中打开。他悄无声息地进来,伏在母亲身上,我在惊恐中在轻轻抖动摇晃的床上又模模糊糊睡去。 二姐投塘 二姐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中生,她少语,乖巧,遇有委屈,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暗自垂泪。她嫁给了村对面山那边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我们以为她从此找到了一生幸福的依靠,他也确实一辈子就认定且娶定了她这个女人,但这依然无法抵抗无常命运的猝然一击。 年初夏的一个午后,我在塘墀职技校校园依依垂柳下,凝神而饶有兴味地看一场乒乓球桌上的师生“龙虎斗”,邻村的一位学长和我招呼:“快回家吧,你二姐跳水塘了!”二姐也撇下她年幼的孩子走了。产后抑郁夺走了父母第二个活蹦乱跳的女儿。父母为着大姐、二姐,求神拜佛、烧香许愿、请道士做佛事、请仙姑讨解药的一幕幕,又过电影一般在眼前闪过,我还记得母亲和紧紧搂抱着幼儿的二姐无助而一脸虔诚地望着仙姑的带着渴望的眼神,愚昧无知的人啊,我真恨不能跳回去甩那时的自己几个巴掌。 母亲的耳光 门前的柚子树苗拔节生长,屋后的竹丛散发蔓延。二哥、三哥相继娶媳妇,这是一个家庭的大事。看场地、送礼、过定、结婚,一个个礼节,都不好怠慢。父母年纪渐大,而家庭大事仍需他们当家作主,周旋周全。那个时候,父母喜在眼里,愁在心头。办这样的喜事,家里总是缺钱,只得拉下面子向亲戚朋友借。愁借不到钱,愁借到了钱后该怎么还。那时,昏黄的煤油灯下,总见母亲盘算借钱的亲友,一个个罗列,又一个个推敲,她一边无奈地摇头,一边轻声地叹气。 看得见生活的希望了,但可见却不可求,那一种绝望让父母痛彻心扉。年金秋时节,稻谷金黄,高粱火红,我考上了一所师专,释放了一下年迈父母脸上的愁容,他们的小儿子大概不用他们那么操心了,我也想着,我如成家,再不让父母那样为我借钱、愁钱了;但我却更伤了他们的心,他们原指望我从此跳出农门,过上坐办公室、不再卷裤腿下田的日子,而我却给他们带回一个邻村落榜的女同学。说通不了我,受了一辈子田地里的苦的母亲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老泪纵横,嚎啕大哭:“你为什么就这么犟,这么傻啊,刚跳出火坑,又要跳回火坑啊?!” 女儿一个个嫁了,儿子一个个娶了,父母也六七十岁了。兄长们一年到头大多外出谋生,孙子孙女们便被一个个扔给年迈的父母照看。他们就像当初抚养自己的儿女一样,为孙子孙女烧饭,洗衣,牵挂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健康平安。 老樟树下的背影 他们一辈子都这样,彼此很少言语,他们一个一瘸一拐地像牛一样不知疲倦不分早晚地在田间地头犁,一个一进一出地像驴一样不紧不慢不黑不白地围着灶台转。他们把话说给了田地里的稻麦蔬菜,庭院里的猪羊鸡鸭。 父母就像大地面对天空一样,承接着天上抛下的风、雨、霜、雪、冰雹和阳光。阳光总是那么吝啬,他们忍着,受着,也抗争着。他们以他们的眼光,让兄长们继承乡间手艺,让我读成了书,为女儿们选嫁好人家。 他们也有无法忍受、想躲避逃避的时候。年一个春日,母亲只身一人,提着小包裹,找到只我新婚时到过一次的我工作的乡村中学。那会我正备战一场入城考试,我埋在备考的书堆里,找不出空闲陪她聊天。母亲第二天便收拾了包裹,决意回家,我送她到校门口的老樟树下,母亲迟疑了一下,停下脚步,说,这次心里不痛快,原想在你这避个七天八天的,你这么忙,妈就不打扰你们了。话毕,转身就走,任凭我怎么喊,她再也没回过头来。母亲越走越远,背影越来越小,我看不见母亲的表情,但校门口那一株老樟树树皮龟裂、枝叶繁茂、一片荫凉,一直在记忆里葱郁。 60岁时,母亲胃下垂,医院住院,花去多元,后来总是念叼,一下花了儿女那么多钱。80岁时,母亲旧病复发,在家里拖着,一周不愈,奄奄一息。小妹急了,电话我,我跑回去,母亲蜷缩在小小的竹床上,喃喃自语:“年纪大了,好不了了,是该走了……”我抱起她,枯瘦,轻盈,就像抱着一只病鸟,那个风风火火的母亲飞走了,怀里是因病痛而瑟瑟发抖的羸弱的身躯。医院,是胃下垂兼胆结石,住了院,母亲又健朗地自由来去了。 钻石婚姻 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脾气也日益温和下来,他们还守在亲手建造的那栋老屋里。父亲在东房,母亲在西房。父亲饭量都好,就嗜睡,一天到晚就好个床。母亲一见了我们就说,这怎么行呢?一天到晚睡在床上,手脚会没力的啊,要到处走走才好。说完母亲就笑自己,我一个人呆不住,我是一有空就得到村子里走走的。 生活常让父母亲失望,甚至绝望,但他们从未放弃过,他们把自己活成了钻石。正月我回家,问他们:“爸、妈,你们还记得哪个日子结婚的吗?”老俩口凑过来,核桃似的脸绽成菊花:“哪还记得呀?哪个季节都想不起来喽!”“妈,你和爸结婚70年了,你知道吗?”“啊,这么快呀,我们哪会记这个哦!” 看着凑在一块的父母亲苍老而欢愉的脸,我眼前闪现的是记忆里那些平日难见的农忙时节温馨的一幕:母亲用冷水打湿的毛巾,从热气腾腾的饭甑里,端出一碗香气扑鼻的腊肉鸡蛋糯米饭(有时是桂圆鸡蛋或红枣炖鸡),轻轻放在父亲桌前。 钻石,洁白,璀璨,稀少,珍贵。它和父母亲的婚姻这么违和,又这么匹配。他们没有结婚证,不识几个字,没有爱情誓言,但他们一遇就是一生。 父亲手植的那棵柚子树虫蛀已折,只剩残根,旁边长出的一株桑树又一人多高了,屋后那丛翠竹已连绵成林,青翠蓬勃。那年的新娘已90岁,那年的新郎已87岁,一身秀发、一头乌发,都已满覆霜雪。70年的婚姻,是钻石婚,这是小山村的头一对。 钻石之恋,是父母的生活之恋,儿女之恋,家庭之恋,情感之恋,是一个四世同堂、60余人大家庭的生活矿藏。 古典爱情 年初我去了一趟铜钹山婚姻民俗文化主题景区鹊桥谷,火红的灯笼,鲜红的婚联,大红的花轿,亭台楼榭廊柱上刻满的爱情诗词佳句,我一下就想到了父母70年的婚姻。父母亲并非青梅竹马,未曾人约黄昏,也不举案齐眉,但他们一生,也如这些经典的爱情,一旦相遇,就是永生,这是多么《古典的爱情》: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谁为谁凝眸? 月上柳梢,人约黄昏, 谁为谁等候? 洞房红烛,花好月圆, 谁与谁牵手?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谁共谁白头? 大红花轿岁月里晃悠, 晃走春光晃来了金秋。 万千青丝转眼中白首, 多少回梦里又掀起那红盖头。 古典的爱情是一坛酒, 时间越长味道越醇厚。 古典的爱情是一支歌, 轻轻一唱就陶醉在那心里头。 作者简介:刘诗良,上饶市广丰区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有歌词、散文等在《词刊》《散文选刊》等各类报刊发表,歌词曾谱曲入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共青团中央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全国少儿歌手电视大赛推荐歌曲首”,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散文曾获江西省旅发委主办、江西日报社承办的全省首届旅游美文征文大赛一等奖。光阴文化促进会负责人。 主编短评: “没有结婚证,不识几个字,没有爱情誓言,但他们一遇就是一生”,文中的这句话正好概括了父母相扶相携的一生――七十年的爱。中国上一辈的老年夫妻,通常不会把“爱”字挂在嘴边,而是藏在心里,偶尔透出爱的意思,也是以“骂”的话语形式出现,这也正是一些年轻作者写这类散文时难以把握的地方,因传统的夫妻之间的爱,如本文所写,先是被一架花桥促成夫妻关系,再像陌生人样整天不是相互黑着脸就是吵吵闹闹过日子,接着开始承受许多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都要应付得整日喘不过气来了,就根本不在乎这生活该爱还是该恨,渐到年老时,潜伏长久的爱或恨才慢慢苏醒,但已不知怎么表达了,这时即使恨也成了爱。爱是一个永远不容易令人明白的词语,它存在于日常生活,消失于尘世烟云,回顾却成一条“弯曲,陡峭,有时甚至足临悬崖或深渊”的道路。所以作者最后如歌似泣地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谁共谁白头。” 文中主要内容按时间先后叙述,小标题下刻画父母生命中某些特殊经历,痛苦多于快乐,沉重透出微叹,这种以点线穿行的写法,让人一读明白,但少了些因缺乏复杂叙事而难以营造更浓郁的氛围,情感所表达的深度就显单纯且单薄了。因每章节相互连贯,又首尾呼应,尤其结尾歌咏式的语言,活络了全文,表现出刘诗良诗意才情和他非同一般的思考力。 《城市笔记》约稿发表在《城市笔记》的作品,稿费标准:字内元,字内元,字以上每篇元。约稿以千字小小说和散文为主,优秀作品字数适当放宽至-字内,诗歌及词择优刊发,并配发相应的主编短评。来稿请附作者近照及简介,每周日出刊。 ■栏目主编:刘树林■ 投稿邮箱:aacsbj . |